文 | 陳飛豪
由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與臺北市立美術館主辦的「當代策展的新挑戰——國際論壇暨青年策展工作坊」中於第三天(10月13日)的論壇中即以「策展與藝術史的構建」為主題,邀請香港M+視覺文化博物館的希克資深策展人皮力、國立臺灣美術館(簡稱國美館)助理研究員周郁齡、任職於法國巴黎東京宮的策展人尤恩・古梅爾(Yoann Gourmel)、立陶宛作家與策展人瑞牧德斯・馬拉薩斯卡(Raimundas Malašauskas)以及現任教於菲律賓大學迪里曼分校藝術學院的艾琳・黎加斯比・拉米雷斯(Eileen Legaspi Ramirez)參與發表並討論,並由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專任副教授郭昭蘭與策展人蔡明君擔任主持與回應人,共同探討策展與藝術史如何構建的議題。

香港M+視覺文化博物館的希克資深策展人皮力以「作品或 / 與 / 及觀念:美術館情境下的策展與歷史建構」為講題。(立方計劃空間提供)
霸權中心的產生與邊緣者的主體性凝聚
「從前從前,有段被稱作現代藝術史的歷史……。」這句話相信是策展人古梅爾在這次演講中,重要的貫穿理念與思考中心,他也以自己曾參與的策展計畫「美國花」(Les fleurs américaines)為例,探討「策展」如何影響與建構一套新的藝術史論述。該展覽由紐約的花園街沙龍(Salon de Fleurus)與柏林美國藝術博物館構思,應艾洛迪.羅耶(Elodie Royer)和古梅爾的邀請而展成,展覽架構共三個章節,其中的部分內容直接指涉了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簡稱MoMA)的創始館長阿爾弗雷德.巴爾(Alfred Barr Jr)在1936年所策劃的「立體主義與抽象藝術」、「奇幻藝術、達達和超現實主義」以及由策展人陶麗絲.米勒(Dorothy Miller)的「美國藝術五十年」。「美國花」展覽以這些策展隱喻了「現代藝術史」的被建構過程,並且直指米勒的策展與MoMA的許多巡迴展覽都帶有文化宣傳的意圖與操作,進而讓美國成為二戰後的藝術霸權。而有趣的是,這個展示幾乎使用畫作複製品與相關的文獻資料檔案,隱喻西方現代藝術史觀的「被建構性」,其中也曾引來畫作的典藏單位抗議,但策展團隊不以為意,並認為對藝術檔案的限制使用,其實也是霸權控制的一種。

相對於戰後以美國為首的藝術史觀建立,歷史進程上剛結束日本殖民即受到冷戰與美蘇對抗情境影響極深的臺灣:一個在不同強大文化主體邊緣生存,且自身意識凝聚尚為初生之犢的島嶼,在自我的策展以及藝術史觀建構上是如何發展?在周郁齡的分享當中,則是做了完整的介紹。根據她的說法,1980年代美術館時代開始後,這類以建立藝術史為目標的策展也慢慢出現,顯示出這類大型的美術史展如何代表機構在臺灣藝術史建置時的觀點與方向。
舉例來說,由國美館與雄獅美術合辦的「臺灣美術三百年作品展」(1990),借重雄獅美術長期在鄉土運動累積的美術論述成為此展重要的基礎。當時在展示上,以媒材分類(中國畫類、西畫類、立體造型、素人創作)再佐以「受中原文化的薰陶,繼而受日本殖民現代性的影響、加上西歐美國文化洗禮」的政治時間序列進行展呈,以看似中性的媒材分類與時間續流陳列,博物館被塑造成真實歷史的敘事空間。不過這樣的策展方法勢必也有可能造成一個僵化的論述狀態,例如攝影史的建構之上,就非常難使用這類以媒材風格結合時間排序的形式論述,在當下館內對此的延續討論中,也有意見直指這類以媒材、年代與風格分類的策展方法,在當代藝術也失去其有效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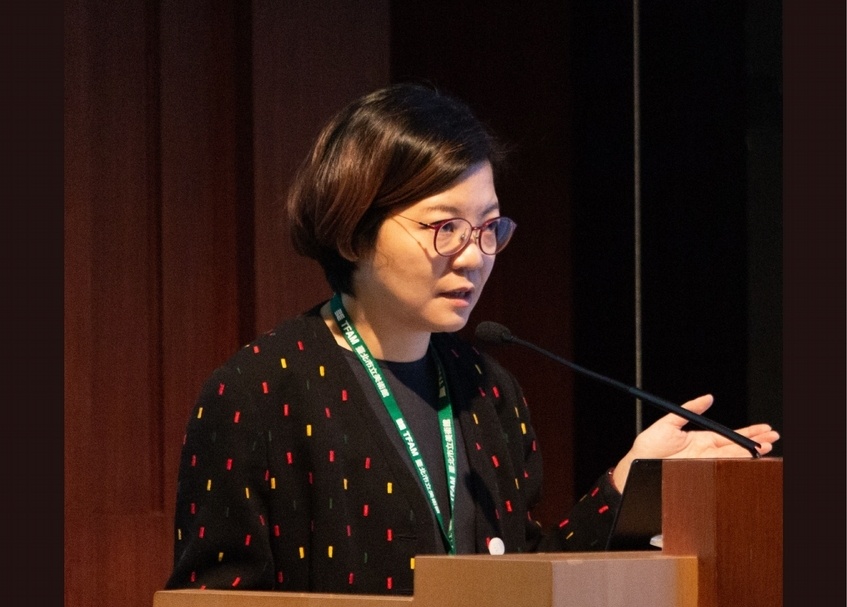
對此,周郁齡則以藝術家蘇新田個人的製史工作為例,探討各種翻轉線性敘事的可能,當時他透過友人購買許多歐美與日本的現代藝術史書籍,並開始對歷史的製圖學產生很大的興趣,因此畫了許多另類的歷史製圖,譬如說,《臺灣共產黨歷史》與《臺灣美術史總年表》等,因為細緻到希望呈現出各種事件的脈絡,並將可能影響的因素並置,他的最後製圖通常都非常凌亂,在如同岩層堆砌以及內爆式的資訊傳遞之下,給予了跨越線性時空的嶄新想像:在混亂之中開啟未知與嶄新連結。而這也是當代策展人回應藝術史想像與當下議題時常見的方法。

原本「被忽略」卻被拉回圓桌會議的中港關係
呼應周郁齡的觀點,皮力則以一名核心研究為古典世界遺產,以及西方文化各領域到文藝復興時期古典表現傳承的阿比.瓦爾堡(Aby Warburg)在身後所留下的各種藝術檔案與拼貼作為對照與解析。在他的這些拼貼版畫中,視覺性的連結大於論述性的整理歸納,以一種個人私密的想像與選件,拼貼出他個人認為的,奠基於古典歐洲的美學想像世界,啟發了西方面對藝術史建構時的策展新方法。不過現今在香港反送中運動如火如荼進行的當下,皮力此次演講幾乎只談論西方的論述觀點,作為香港重要美術館的代表人,卻完全忽略香港的策展發展現況,在政治情勢的對比之下,著實令人感到耐人尋味。我們很難不注意這樣的「忽略」。馬拉薩斯卡就直接在皮力演講後的問答時間中微妙地建議,「這裡其實是一個學術性而非政治的場合,您(指皮力)其實可以不用那麼在意。」而這一系列關於香港問題的討論也延續到當日最後的圓桌會議。

但或許是過於注重「國際化」而讓皮力的演講充滿了西方論述,而讓他僅能使用較少的演講篇幅討論香港當下的藝術實踐情形,例如他所談到的以水墨、漆器等以媒材為基礎的探討方向,雖然可以跨越國界與文化語境,但是似乎也還是回到如周郁齡談到類似臺灣1980至1990年代時,以媒材與時間進程為主的策展方向,與他引用瓦爾堡以藝術史中的視覺符號串連發展出議題想像的狀態相差甚遠。臺灣與香港有點相似但又完全不一樣的地方是,我們在脫離帝國殖民統治後進入另一個外來政權的統治時期,雖然當下政治系統運作的狀態不盡相同,但這樣具有相似性的歷史環境,如何牽引著臺港策展人與藝術家們的思維與方向,事實上會遠比今年在國美館「共時的星叢」一展中其實就已借鏡的瓦爾堡之觀點更能吸人目光與省思,更何況這個展覽還進一步地討論了戰前臺灣美術的前衛性想像。(註)而這個不知是否是刻意的「忽略」或「被缺席」,事實上是整場論壇的一個遺憾。


除了上述三位策展人的分享,此次論壇亦有艾琳・黎加斯比・拉米雷斯針對她所任教的菲律賓大學,以與佔據校地邊緣族群合作的藝術工作坊與展出作為自身的經驗分享。馬拉薩斯卡則是將演講轉以略帶詩意性的「Lecture Performance」分享自我的藝術經驗。本次論壇的中心思考在於策展與藝術史建構間的關係。以機構為發展基礎的藝術史專題策展,當然可能成為西方霸權文化輸出的重要形式,但是邊緣者如冷戰夾縫下的臺灣在這樣的方法學參考下,如何修正進而得到了怎樣的啟示發展出自己凝聚主體性的一套建構方法?也是慢慢地有了一定的發展雛型,而在這當中方法也只是方法,會凝聚出怎樣的新想像,也考驗著策展人與藝術史系統的互動技巧。

註 陳飛豪,〈共時的星叢.形式的邊界.留下的未竟: 日治臺台灣與風車詩社擴延出的視覺感性先行與前衛性〉,《典藏.今藝術&投資》,323期,2019.08,頁112-115。









